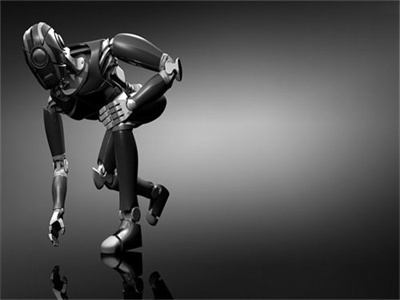姜月周容深讲的什么-夜宴姜月周容深最新章节
他沉默不语,我对准他鼻梁呵出一口酥酥麻麻的热气,“如果痒就告诉我,进船我给你吹一下,吹到你解痒好不好。”
这么色情的挑逗,这么直白的勾引,我和黑狼两张面孔之间迅速升温,烫了他的眼眸,也烫了我的媚笑。
我只顾着说话,不曾留意到脚下湿滑,在扑向他怀中时没有站稳,朝后面踉跄翻倒,在我坠地的前一秒他手臂迅速揽住我的腰,将我托起纳入我顺势勾住他脖子,在他唇上我的我伸出舌头探进去,他牙关起先咬得很紧,在我锲而不舍的扫荡攻克下,终于无声无息缴械,勇猛吞噬了我。
他口中是浓烈的烟味,是醇厚的酒香,是让我迷醉沉沦的男人狂野的气息,我贪婪吸取着,我的芬芳和香甜将他的猖獗溶解,淡化,驱散,他吮得我舌根发麻,我开始逃脱那股令我窒息的阳刚,逃脱他的纠缠和撕咬,是我先诱惑他,诱惑他难以克制,他誓不罢休侵占我唇内的每一处,我感觉到他舌头狠狠抵入喉咙,我口干舌燥,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津液,渴得连呼吸都是沙漠。
他恨不得用舌头狠狠贯穿我,一点点蚕食,将我粉碎。
我逃离他的唇,和他鼻尖挨着鼻尖,“你想不想和我做爱。我要听实话。”
他急促喘息着,眼底逐渐不再那么清明,染了一丝浅浅的火焰,我期待望着他,他最终没有抵御住我灼热的目光,低低闷笑出来,“有一点。”
“一点是多少,到了夜不能寐的地步吗。”
他凝视我近在咫尺的红唇,“这么贪心,想要勾引我失眠。”
“最毒妇人心,你没听过吗。”
我和容深的第一夜,我是被他征服的。
不是他的官位,不是他的权势,也不是钱财和他的皮囊,而是他精湛的床技,他吃遍我每一处的狂野,我人生第一次巅他低低吼了声,额头隐忍出细细的薄汗,他一把扼住我手腕从拉链内抽出,利落系好,身后的灯火闪了闪,第二艘船舱内走出的马仔没有看清岸上场面,他大声喊五哥,黑狼立刻推开我,走上去几步问怎么,马仔指了指天色,“最晚凌晨两点前装完,咱们出港来不及,能和下家推迟吗。”
他目光眺望远处黑暗起伏的海面,“不能,再加派人手,一点必须走。”
马仔面露为难,“下家不是很急,再派人手动静太大,怕巡逻的条子察觉。这已经四十多个人了。”
黑狼手伸入口袋,摸出半支雪茄,港口风烈,点不着打火机,他拿两枚火石用力一擦,火光四射间,烟头也燃烧起来。
他吸了口,烟雾缭绕他的半张脸,“条子来不了。”
马仔听他这么说,只好又从附近街道调了一些喽啰兵,码头来来往往一片热火朝天,我坐在甲板边缘,两只脚在水面浮荡,打碎了月光,打碎了树影,打碎了这凉如水的云南之夜。
黑狼站在最高的船头指挥,偶尔转身看我一眼,我便往他身上泼一点水,咯咯娇笑着,如此反复几回,我知道火候差不多,不如留下无限遐想回味。
我悄无声息跳下甲板,朝巷子口等候我的阿碧飞奔,我一秒没停歇,拉住她的手穿过阴森破败的深巷,身后彻底远去的一刻,我忍不住回头,这夜幕下的湖海,灯火阑珊的港口,他眼中的我,我眼中的他,转瞬失了踪影。
目睹了我和黑狼痴缠的阿碧问我,“那男人和您早就认识吗。”
我坐在车里透过玻璃张望空荡无人的街口,“也许是。”
她一怔,“也许?”
我食指抵在上面,重合昏黄的路灯,再没有开口。
第二天是云南特色庙会,阿碧告诉我紧挨景洪的一趟古街很热闹,我在宾馆正好待得无聊,就打扮成当地女人的模样,在午后上了集市。
没想到这一趟竟然遇到熟人,特区福寿山庄曾老板的续弦夫人,带着两名保姆和我恰巧走了碰头,我起先没有留意,她认出后让我留步,我这才看清是她。
阿碧拿着灯笼剪纸退后几米,曾夫人喜上眉梢,“我先生带着女儿去国外看秀,留下我自己守着大房子也无趣,听说云南洱海很美,我顺道来逛逛。”
我隐瞒了来这边的真实意图,省得她传回去闲话,我在金三角一面与市局通气,一面做不可告人的事,暴露越多越棘手,我扯谎说我也是刚从洱海回来。
她诧异问,“周太太来了多久。”
我估算了下日子,“一周了。”
她呀了声,“那想必广东的事您不知道了。”
她挥手示意保姆走远点,然后拉着我的手站在一间商店的屋檐下,“蒂尔与盛文合并了,此后就是盛文的分部,再也没有蒂尔一说了。”
我凝视地上倒映的人影,乔苍承诺过蒂尔永远是独立存在,他掌控却不会吞并,他最终还是食言。但他食言也是我的缘故,我朝思暮想容深,与黑狼勾结不清,他恨我固执,恨我不听话,借此给我一个教训,让我知道背叛他的下场,就是什么也守不住。
我掸了掸腰间火红的流苏穗儿,“无妨,反正也是乔苍在控制,一点虚名而已。”
“还有呐。常小姐在珠海入院,到现在还没出来,听说伤了女人的根。”
我蹙眉,“女人的根?”
“她子宫破裂,摘除了,从此再不能生育,甚至不算个女人。”
我手一抖,险些把穗子扯断,“怎么会。”
曾太太幸灾乐祸笑,用手挡住唇,眼睛机灵四下看,“听华章赌场传出的消息,那不是乔先生地盘吗,里头马仔的话可信。她总急着怀孕拴住乔先生,吃了不少坐胎的药,可那些药都有问题,吃寒身子了,五天前忽然大出血,差点没保住命。虽然救回来,可她似乎知道了什么,神情恍恍惚惚的。乔先生据说也不在,没得空回去,她也不问,她那么娇生惯养,出了这么大的事不找自己老公。周太太聪慧,您给分析下是怎么回事。”
常锦舟这样狼狈凄惨的下场,明显蓄谋已久,能够在她饮食用药中做手脚,没有乔苍的默许,谁有这个胆子。
我曾太太感慨万千摇头叹息,“她出身名门,老子那么厉害,又嫁了乔先生,素日傲气得不行,老子和先生在场时装贤淑温柔,私底下跋扈的臭德行,惹了多少富太太不满,都说她活该,没人去瞧她。”
她话锋一转,有些怜悯,“她还不到三十岁,女人的路算是断了。”
我良久沉默,曾夫人的保姆催促她趁太阳落山前回去,她和我道别,她离开后我仍有些恍惚,站在台阶上失神,阿碧等了片刻招呼我往另一边走,我拍打她手上挑着的灯笼,“你有没有经历过风月。”
她说没有,从小习武,都在武馆过的。
她附在我耳畔小声嘀咕,“成天就知道踢胳膊踢我被她逗笑,拐出这条长街时,右侧一辆黑车忽然按了按喇叭,尖锐刺耳的笛声乍起,仓促惊吓了我,我朝后退半步,紧盯这辆包抄了我前路的车,形状颜色都很普通,或许因为崭新的缘故,不仅夺目,更像是伏击的猎豹一般,从楼宇角落,从拥挤人潮忽然蹿出,我嗅到敌人的味道,脚下不由自主迟缓。
茶色



 作业完成的好表扬语优美句子(27句)
作业完成的好表扬语优美句子(27句) 20个英语最高级的句子
20个英语最高级的句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