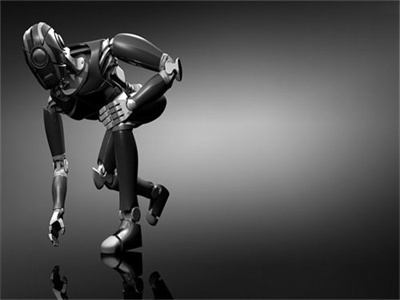抖音高赞小说地乌金在线阅读罗敷季庭柯新上现代言情小说推荐
雨稍微小一些的时候,罗敷爬上了煤一中家属院、最高一栋楼的天台。
天台有钢管捆的晾衣杆、过去养鸡的鸡笼,小孩丢弃的溜冰鞋、淹透的摔炮儿。
女人倚着锈顿的围栏,终于看得更清、更远:她看到,几乎被夷为平地的荒土上,煤一中家属院是唯二的建筑。
另外一块地,是一片有着蓝色铁皮屋顶的、巨大 破旧的厂房,隐约可见过去繁华,吊车头绰绰地抛出来,紧挨着一条细长奔流的河。
河的上游,二三百米处,是一个小水电站,为钼矿场提供廉价而充沛的电力。
隔着远,罗敷看不见掩在厂房下的矿井有多深,她只能大致观测出那矿场逐渐挖掘到城市边缘,像一道深刻、触目惊心的疤痕。
她不在以“功勋矿山”享誉盛名的可可托海,她在臭名昭著、吞噬数百人姓名的钼矿之上。
因煤而兴的小城,落寞到如今一场雨灌下来,方圆一公里内,只有一家水果店支起了蓬、匆匆甩卖。
罗敷买了两把香蕉、一兜葡萄、一袋无花果。
想了想,又折返回去,买了一箱梨。*
杨婷已经出院一周有余。
雨落过后、她出门扔垃圾,一推门,直挺挺地撞上一地的水果。
旁边还有一摊快要干涸的水渍,人似乎已经走远了。
郝响扒着门缝,他蹲下身来看阶上一串水印子:
“是季叔叔来过吗?”
“可能吧。”
杨婷搁下垃圾,给季庭柯发了个消息。
她说:不用再买东西了,家里就我和小响两个人、吃不完浪费。配图一张。远在园区。
季庭柯摘下安全帽、他盯着那张照片,慢慢地输入:不是我。
三个字顿在状态栏里半晌,似乎联想到什么、又删除了。好的,他说。:我知道了。**罗敷跟着张立超、在煤一中附近徘徊了近半个月。
如今,她扔掉了这将近半个月以来买的所有累赘衣物、帽子、墨镜等其余一次性用品,退了酒店。
当天,临近傍晚的时候,罗敷终于折返、再次回到了园区附近。
她的黑包、相机还寄存在那周边的大鲨鱼网吧。
还是那个年轻的网管,面上的绒毛在顶光下一览无余,他瞥了一眼罗敷,眼里毫不掩饰的讶异。
她问:“我的东西呢?”
网管腹诽着,往后指了指。
它们镶在角落里,再往后是开台的电脑。
一个男人背对着罗敷、露出骨节分明、青筋暴起的小臂。
罗敷将包甩到了身后。
拿到东西后,她并没有立刻走。
而是耐心等着、直到那嵌着滚轮的椅子滑、转过来——是季庭柯。
他还穿着灰色的工服,起身、靠近她。
“来这里上网的人都说,有个女疯子——行李寄存在网吧,半个月了也不来取。”
罗敷用指节扣上对方工服的领子,她“哦”了一声、低声说:
“所以,你在这里是…?”
季庭柯转过眼,对上网管、身边人探寻的目光。
他替身边打游戏的扶正了头戴式耳机。
确认对方的耳里充斥满了打斗声、配乐,确保对方听不见他说:
“我在这里,是为了等一个女疯子。”
杨婷门口堆砌成山的水果,是罗敷的歉意、也是她通过对方,隔空掷出的预防针。
那一针扎扎实实地戳到季庭柯的肉上。
自那一则消息起,他一直在等她。
像如今这样、在大庭广众之下,旁若无人地垫脚在他耳边吹气。
网吧的台桌上还放着一杯茶,几片茶叶悬在开水上飘,一处小小的漩涡,要将罗敷黑色的瞳仁吸进去。
“季庭柯。”
“嗯?”
“我知道了。”
“知道什么?”
“全部。”
男人闭了闭眼,像是有所预料一般,他压着女人的后脑勺,任凭对方的牙撞上自己的肩,发出被遏止住声音的动静。
“换个地方说话。”**园区附近,大鲨鱼网吧的后头,有一家很俗的私人酒店、名叫“可蒂”。
可字灯箱坏了一半,只剩个“口”。
店前有五个台阶,罗敷单手拎着背包。
直到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支着腰过来,怡怡然去帮罗敷拎手中的包,小臂明显蓄了力。
“我操。”
“焦化厂不有运煤专线么,怎么如今沦落到、用包装煤了。”
是嫌弃包重的意思。
女人调侃、美目转了一圈儿。
她的目光落在罗敷身后、季庭柯的脸上。
认出来了,又漫不经心地回前台操作电脑。
季庭柯在这间隙,脱了他灰色的工服,露出背心、结实的肌肉。
他把印有“盛泰轻合金”刺绣的那一面朝下、团在手心里。
罗敷说,“要一间大床房。”
她问:“你们这里,隔音怎么样?”
女人收了押金,给对方拍了照,她笑得暧昧——
“一楼隔音不太好,要小点声。”
又招呼季庭柯,“你的身份证呢?”
“他不用。”
这句话,是罗敷说的。
“说两句话,我就走。”
这句话,是季庭柯说的。
陈可蒂生意做过许多年。招待过煤老板、小工、前头泡吧的网虫。
她头一次见来开房的,人前装作不熟,人后——眼里复杂、垫积的火光都快溢出来。
罗敷的眼神始终放在季庭柯身上。
季庭柯的眼神,同样、始终落在罗敷身上。
他们看上去像是在人前会扇对方一巴掌的死对头。关了门、一本正经地谈事,谈不拢、就开始互甩脸色。
冷着脸,把她的床做塌。
她拍了房卡在桌上,往前推了推。
而后,那张房卡被女人用指尖捻着带走。
他们往一楼的房间方向去,从陈可蒂的角度,能窥到关门的一瞬:罗敷猛地抬高头,对方长长的卷发海藻般落下,她似乎撞到了男人的鼻子,被季庭柯捏着下巴、忍无可忍地推进去。
陈可蒂谨慎地,捂住了耳朵。***三十平的房间,他们只挤在一处。
季庭柯拿了热水宝烧水,又开了浴霸,两方声音较劲地冒。在此之下,谈话声显得微不足道。
罗敷坐在沙发上,点了一根烟。
她饶有兴致地拍了拍身边的位置,神色不明地。
“坐过来。”
季庭柯双眼黑漆漆地,他沉静地盯着她。
沙发陷下去了一小块,罗敷顺势躺了下来,仰在季庭柯的腿上。
她摸了摸他生着青色胡茬的下巴。
“这是谈判的姿势吗?”
男人滚了滚喉结,他说话时胸腔震动,罗敷的脑袋抵着、紧跟着一麻。
她说:“是。”
“半个月没见我了,你不想我吗?”
她抽剩的半根烟,被塞进了季庭柯嘴里。
一簇烟雾鼓出来,罗敷几乎看不清男人的脸。
她摸着他紧实的大腿肌、流畅的腰线。
她说:“我是来告别的,季庭柯。”
季庭柯把烟头淹在了指尖,他匪夷所思地看着她。
“去哪里?”
“如你所愿,回韫城。”
女人深吸了一口气,她起身、额头轻轻贴上他的。
“我会把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忘了。”
罗敷移开了目光,微微眯着眼。
当着季庭柯的面,她滑开了手机。彻底删除了郝国平、曾经发送给她的那封邮件。
导致他们纠葛、交缠的罪魁祸首。
季庭柯一下拉住了罗敷的手腕,他将她整个攥紧了,脸离她很近。
罗敷和他共享了这一小方的呼吸。
“从医院回来后,我又去了煤一中家属院。”
“不止一趟。”
她笑了笑,季庭柯能闻到她身上浓郁的烟草味。
“我见到了张立超——张立超,你认识吗?”
“他的父亲——张永任,身故在一期爆炸中,赔款一百二十万。这一百二十万,买断了老子的命、又救了儿子的命。”
她轻轻咬着牙,近乎气声地:
“我知道,他们是故意的。”
季庭柯眼皮颤了一颤。
罗敷又说:“我还知道——煤一中附属院附近,那边的地下埋了什么。”
她发狠地咬上他的虎口,铁锈味在口腔里溃开。
“季庭柯,别死在这里。”
用他曾经告诫过她的:永远、永远不要接近矿区。
季庭柯强硬地掰开罗敷的脸,他两指屈起来、撬开了女人的嘴。
他的手指伸进了她温热、紧实的口腔。
他捏住了她的舌尖,一点唾液、加上一点血迹。他的血。
他说:“你错了,没有人是故意的。”
“那算什么?”
“算顺水推舟、算老天爷不长眼。”
男人托着罗敷的腰,他把她往上抻了,她坐在他的胯间,小腹紧挨、一片火热。
“模盘结晶器漏铝,是确有的事故。”
“夜班的工人发现漏铝没有阻止,是一类做法。停止铸造、紧急排放模盘中的铝液,而是违规使用金属棍撬压。也是一类做法。两方,都会导致爆炸。”
季庭柯寡淡地笑了笑。
“报道的都是真的。没有人隐瞒、捏造事实。”
“是郝国平,起了那个念头。”
至于张永任、宋淑珍、姜良桂、邓恩龙——
“他们都是三期。没有钱的下场是什么——活活被憋死?”
“他们不过是没有阻止,默认了自己的死亡。”
季庭柯也尝到了罗敷口中的血味。
这是他第一次、主动贴上来接吻。
她的眼睛被捂住了,触感更加真实。
她掐住了季庭柯的领子。
他干燥、皴裂的唇被她咬在嘴里,只能含含糊糊地——他说:“那天晚上的值班表,是我让人调动的。”
季庭柯摩挲着罗敷的眼皮,直到她眼珠动了动、在他的掌心轻轻剐着。
“那是个周日。第二天,一早有省医院开展的尘肺义诊活动,只要是参与的、都会送一瓶治疗慢阻肺的药——大夜班之后,次日白天会倒休。
是我,自作主张、想让他们去。”
至于曾翔,属实是个不幸的意外。
他是小夜班,也就是夜里十二点之前交班。
好巧不巧地,那晚他将手机遗落在了叉车上。
折返回来找,恰好迎面撞上那朵盛放、璀璨的火花。
曾翔在热浪的冲击下飞了出去,他看到一期厂区所有的玻璃、门窗都炸得碎裂,其中一小片、深深地扎进了他的眼里。
索性,宿舍楼离一期工程较远、并未受到影响。
不知是谁喊了声——
“爆炸了!”
那是一切的起点、一声拉开帷幕的号角。
屋子里出奇地安静。
季庭柯的心跳扑通、扑通,几乎要敲晕了罗敷。
男人状似冷静地贴过她的嘴唇,顺着下巴、脖颈、用牙咬开她胸衣的金属扣子。
像猫舐伤口,罗敷察觉到自己胸前、一滴温热的液体落下。
月色中天,有人向月亮祈祷。
有人支起桨,在夜里航船。
这俩虽然在谈判交流但行为都好sexy......你怎么知道下一章就是sex ⌯ᵔ⩊ᵔ⌯ಣ好想把推荐票都送给作者 太好看了。
好(伸手)
天台有钢管捆的晾衣杆、过去养鸡的鸡笼,小孩丢弃的溜冰鞋、淹透的摔炮儿。
女人倚着锈顿的围栏,终于看得更清、更远:她看到,几乎被夷为平地的荒土上,煤一中家属院是唯二的建筑。
另外一块地,是一片有着蓝色铁皮屋顶的、巨大 破旧的厂房,隐约可见过去繁华,吊车头绰绰地抛出来,紧挨着一条细长奔流的河。
河的上游,二三百米处,是一个小水电站,为钼矿场提供廉价而充沛的电力。
隔着远,罗敷看不见掩在厂房下的矿井有多深,她只能大致观测出那矿场逐渐挖掘到城市边缘,像一道深刻、触目惊心的疤痕。
她不在以“功勋矿山”享誉盛名的可可托海,她在臭名昭著、吞噬数百人姓名的钼矿之上。
因煤而兴的小城,落寞到如今一场雨灌下来,方圆一公里内,只有一家水果店支起了蓬、匆匆甩卖。
罗敷买了两把香蕉、一兜葡萄、一袋无花果。
想了想,又折返回去,买了一箱梨。*
杨婷已经出院一周有余。
雨落过后、她出门扔垃圾,一推门,直挺挺地撞上一地的水果。
旁边还有一摊快要干涸的水渍,人似乎已经走远了。
郝响扒着门缝,他蹲下身来看阶上一串水印子:
“是季叔叔来过吗?”
“可能吧。”
杨婷搁下垃圾,给季庭柯发了个消息。
她说:不用再买东西了,家里就我和小响两个人、吃不完浪费。配图一张。远在园区。
季庭柯摘下安全帽、他盯着那张照片,慢慢地输入:不是我。
三个字顿在状态栏里半晌,似乎联想到什么、又删除了。好的,他说。:我知道了。**罗敷跟着张立超、在煤一中附近徘徊了近半个月。
如今,她扔掉了这将近半个月以来买的所有累赘衣物、帽子、墨镜等其余一次性用品,退了酒店。
当天,临近傍晚的时候,罗敷终于折返、再次回到了园区附近。
她的黑包、相机还寄存在那周边的大鲨鱼网吧。
还是那个年轻的网管,面上的绒毛在顶光下一览无余,他瞥了一眼罗敷,眼里毫不掩饰的讶异。
她问:“我的东西呢?”
网管腹诽着,往后指了指。
它们镶在角落里,再往后是开台的电脑。
一个男人背对着罗敷、露出骨节分明、青筋暴起的小臂。
罗敷将包甩到了身后。
拿到东西后,她并没有立刻走。
而是耐心等着、直到那嵌着滚轮的椅子滑、转过来——是季庭柯。
他还穿着灰色的工服,起身、靠近她。
“来这里上网的人都说,有个女疯子——行李寄存在网吧,半个月了也不来取。”
罗敷用指节扣上对方工服的领子,她“哦”了一声、低声说:
“所以,你在这里是…?”
季庭柯转过眼,对上网管、身边人探寻的目光。
他替身边打游戏的扶正了头戴式耳机。
确认对方的耳里充斥满了打斗声、配乐,确保对方听不见他说:
“我在这里,是为了等一个女疯子。”
杨婷门口堆砌成山的水果,是罗敷的歉意、也是她通过对方,隔空掷出的预防针。
那一针扎扎实实地戳到季庭柯的肉上。
自那一则消息起,他一直在等她。
像如今这样、在大庭广众之下,旁若无人地垫脚在他耳边吹气。
网吧的台桌上还放着一杯茶,几片茶叶悬在开水上飘,一处小小的漩涡,要将罗敷黑色的瞳仁吸进去。
“季庭柯。”
“嗯?”
“我知道了。”
“知道什么?”
“全部。”
男人闭了闭眼,像是有所预料一般,他压着女人的后脑勺,任凭对方的牙撞上自己的肩,发出被遏止住声音的动静。
“换个地方说话。”**园区附近,大鲨鱼网吧的后头,有一家很俗的私人酒店、名叫“可蒂”。
可字灯箱坏了一半,只剩个“口”。
店前有五个台阶,罗敷单手拎着背包。
直到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支着腰过来,怡怡然去帮罗敷拎手中的包,小臂明显蓄了力。
“我操。”
“焦化厂不有运煤专线么,怎么如今沦落到、用包装煤了。”
是嫌弃包重的意思。
女人调侃、美目转了一圈儿。
她的目光落在罗敷身后、季庭柯的脸上。
认出来了,又漫不经心地回前台操作电脑。
季庭柯在这间隙,脱了他灰色的工服,露出背心、结实的肌肉。
他把印有“盛泰轻合金”刺绣的那一面朝下、团在手心里。
罗敷说,“要一间大床房。”
她问:“你们这里,隔音怎么样?”
女人收了押金,给对方拍了照,她笑得暧昧——
“一楼隔音不太好,要小点声。”
又招呼季庭柯,“你的身份证呢?”
“他不用。”
这句话,是罗敷说的。
“说两句话,我就走。”
这句话,是季庭柯说的。
陈可蒂生意做过许多年。招待过煤老板、小工、前头泡吧的网虫。
她头一次见来开房的,人前装作不熟,人后——眼里复杂、垫积的火光都快溢出来。
罗敷的眼神始终放在季庭柯身上。
季庭柯的眼神,同样、始终落在罗敷身上。
他们看上去像是在人前会扇对方一巴掌的死对头。关了门、一本正经地谈事,谈不拢、就开始互甩脸色。
冷着脸,把她的床做塌。

她拍了房卡在桌上,往前推了推。
而后,那张房卡被女人用指尖捻着带走。
他们往一楼的房间方向去,从陈可蒂的角度,能窥到关门的一瞬:罗敷猛地抬高头,对方长长的卷发海藻般落下,她似乎撞到了男人的鼻子,被季庭柯捏着下巴、忍无可忍地推进去。
陈可蒂谨慎地,捂住了耳朵。***三十平的房间,他们只挤在一处。
季庭柯拿了热水宝烧水,又开了浴霸,两方声音较劲地冒。在此之下,谈话声显得微不足道。
罗敷坐在沙发上,点了一根烟。
她饶有兴致地拍了拍身边的位置,神色不明地。
“坐过来。”
季庭柯双眼黑漆漆地,他沉静地盯着她。
沙发陷下去了一小块,罗敷顺势躺了下来,仰在季庭柯的腿上。
她摸了摸他生着青色胡茬的下巴。
“这是谈判的姿势吗?”
男人滚了滚喉结,他说话时胸腔震动,罗敷的脑袋抵着、紧跟着一麻。
她说:“是。”
“半个月没见我了,你不想我吗?”
她抽剩的半根烟,被塞进了季庭柯嘴里。
一簇烟雾鼓出来,罗敷几乎看不清男人的脸。
她摸着他紧实的大腿肌、流畅的腰线。
她说:“我是来告别的,季庭柯。”
季庭柯把烟头淹在了指尖,他匪夷所思地看着她。
“去哪里?”
“如你所愿,回韫城。”
女人深吸了一口气,她起身、额头轻轻贴上他的。
“我会把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忘了。”
罗敷移开了目光,微微眯着眼。
当着季庭柯的面,她滑开了手机。彻底删除了郝国平、曾经发送给她的那封邮件。
导致他们纠葛、交缠的罪魁祸首。
季庭柯一下拉住了罗敷的手腕,他将她整个攥紧了,脸离她很近。
罗敷和他共享了这一小方的呼吸。
“从医院回来后,我又去了煤一中家属院。”
“不止一趟。”
她笑了笑,季庭柯能闻到她身上浓郁的烟草味。
“我见到了张立超——张立超,你认识吗?”
“他的父亲——张永任,身故在一期爆炸中,赔款一百二十万。这一百二十万,买断了老子的命、又救了儿子的命。”
她轻轻咬着牙,近乎气声地:
“我知道,他们是故意的。”
季庭柯眼皮颤了一颤。
罗敷又说:“我还知道——煤一中附属院附近,那边的地下埋了什么。”
她发狠地咬上他的虎口,铁锈味在口腔里溃开。
“季庭柯,别死在这里。”
用他曾经告诫过她的:永远、永远不要接近矿区。
季庭柯强硬地掰开罗敷的脸,他两指屈起来、撬开了女人的嘴。
他的手指伸进了她温热、紧实的口腔。
他捏住了她的舌尖,一点唾液、加上一点血迹。他的血。
他说:“你错了,没有人是故意的。”
“那算什么?”
“算顺水推舟、算老天爷不长眼。”
男人托着罗敷的腰,他把她往上抻了,她坐在他的胯间,小腹紧挨、一片火热。
“模盘结晶器漏铝,是确有的事故。”
“夜班的工人发现漏铝没有阻止,是一类做法。停止铸造、紧急排放模盘中的铝液,而是违规使用金属棍撬压。也是一类做法。两方,都会导致爆炸。”
季庭柯寡淡地笑了笑。
“报道的都是真的。没有人隐瞒、捏造事实。”
“是郝国平,起了那个念头。”
至于张永任、宋淑珍、姜良桂、邓恩龙——
“他们都是三期。没有钱的下场是什么——活活被憋死?”
“他们不过是没有阻止,默认了自己的死亡。”
季庭柯也尝到了罗敷口中的血味。
这是他第一次、主动贴上来接吻。
她的眼睛被捂住了,触感更加真实。
她掐住了季庭柯的领子。
他干燥、皴裂的唇被她咬在嘴里,只能含含糊糊地——他说:“那天晚上的值班表,是我让人调动的。”
季庭柯摩挲着罗敷的眼皮,直到她眼珠动了动、在他的掌心轻轻剐着。
“那是个周日。第二天,一早有省医院开展的尘肺义诊活动,只要是参与的、都会送一瓶治疗慢阻肺的药——大夜班之后,次日白天会倒休。
是我,自作主张、想让他们去。”
至于曾翔,属实是个不幸的意外。
他是小夜班,也就是夜里十二点之前交班。
好巧不巧地,那晚他将手机遗落在了叉车上。
折返回来找,恰好迎面撞上那朵盛放、璀璨的火花。
曾翔在热浪的冲击下飞了出去,他看到一期厂区所有的玻璃、门窗都炸得碎裂,其中一小片、深深地扎进了他的眼里。
索性,宿舍楼离一期工程较远、并未受到影响。
不知是谁喊了声——
“爆炸了!”
那是一切的起点、一声拉开帷幕的号角。
屋子里出奇地安静。
季庭柯的心跳扑通、扑通,几乎要敲晕了罗敷。
男人状似冷静地贴过她的嘴唇,顺着下巴、脖颈、用牙咬开她胸衣的金属扣子。
像猫舐伤口,罗敷察觉到自己胸前、一滴温热的液体落下。
月色中天,有人向月亮祈祷。
有人支起桨,在夜里航船。
这俩虽然在谈判交流但行为都好sexy......你怎么知道下一章就是sex ⌯ᵔ⩊ᵔ⌯ಣ好想把推荐票都送给作者 太好看了。
好(伸手)



 新年祝福语简短大方
新年祝福语简短大方 (徐佳欣沈辰)小说最新章节-(徐佳欣沈辰)全文无弹窗阅读
(徐佳欣沈辰)小说最新章节-(徐佳欣沈辰)全文无弹窗阅读